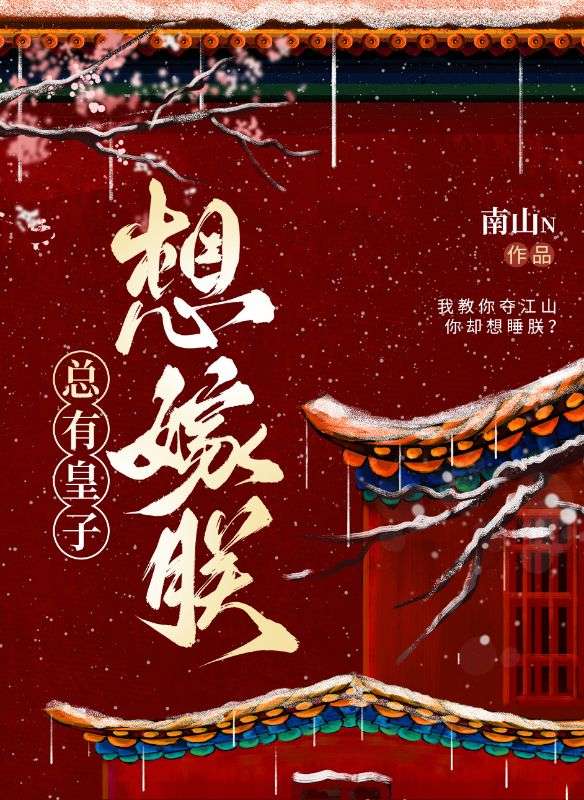
上点众小说APP
体验流畅阅读
第20章
确认
谢世忠笑得意味深长:
“噫!尚书大人也知道?前些日子的确是找了许多舞姬,但男人么,寻常花样腻了,也爱尝新鲜。那些个小倌儿一个赛一个的好看,可不输花魁娘子呢!要不改日同去?”
将离讪笑:“改日饮酒可以,这我可无福消受。”
谢世忠朗声大笑,眉骨耸动。
潘德海出来看到他,立刻躬身相迎:“哟,司公来了,陛下正等着您呢。”
将离同他拱了拱手,告辞而去。
避暑山庄谢世忠虽姗姗来迟,但皇帝事后只罚俸便罢,皇城司依旧牢牢握在他的手中,可见此人非同寻常。
这人面上笑呵呵,实则城府极深,尤其是那双细眼,纵然面上笑意再深,都冷得像淬毒的刀,将离不敢轻易靠近,也不敢轻易得罪。
出了宫,她打发了双庆后,带着琉羽去了城郊的善堂。
慧修最近都在此处。
秋季多雨,马上雨季要来了,最近善堂请人修缮屋檐及各处破损之处,她忙得团团转。
“这回气色倒是好些,药还接着吃,知道吗?”慧修搂着她,看了又看。
“记得,一天三顿忘不了,琉羽都盯着呢。”将离亲热地搂着她手臂摇了摇,“师父,瞧着大事快定了。只等那孟贺嶂进京,我还有些话得问他。”
“苌茗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,信鸽都找不着他。不然也好让他去叶州再探一探。若真是屠光杀了太傅,直接剁碎喂狗!”
将离点头,“叶州有问题,为何孟贺嶂做了二十年的师爷却从未对朝廷提过?涌安收买叶小东换信,二皇子却至死不认。若不是他指使,又会是谁呢?现在二皇子一派已经沉戟,死无对证,走进了死胡同。唯一得到好处的,真就只有皇帝了。涌安难道是为皇帝办事?我总觉得这里头哪不对,可我一时又想不明白。”
能为皇帝办这样机密的大事,怎么也轮不到涌安吧?
谢世忠和他旗下的皇城司又不是摆设。
这便是将离想不明白的地方。
慧修对皇帝没什么好感,自古帝王皆心狠手辣,她认同将离的看法:
“伴君如伴虎,当年若没有你爹授他诗书,他如何能成为大庆帝王。真是狡兔死、走狗烹。按我们话说,就是白眼狼。”
将离眉眼淡淡:“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。爹虽事事谨慎,可将家那些个狗东西没一个不招摇的。”
慧修深以为然,她拍了拍将离的手背,“走,去瞧瞧涌安老娘吧,在里屋。”
她刚想陪着将离一道进去,身后有个娘子唤她:“慧修师傅,这个竹子抬去哪里?”
“哎哟王娘子,你放着放着,我来,别闪着腰了。”
将离回身一看,是个满脸红润、腰背憨实的妇女,正用粗布擦着汗,“不妨事,我最不值钱的就是力气了。”
慧修爽朗一笑,两人一前一后忙活去了。
将离对琉羽道:“这个娘子好生爽利,倒是同师父投缘。”
“也是个可怜人。他相公淹死了,家里仨孩子嗷嗷待哺,平日就在街市上卖菜讨生活,师父接济她,她也懂得感恩,空闲了来善堂打下手。”
将离边走边点头:“师父说得很对,女子嫁了人便是二次投胎,谁也不知自己的命运会如何,惟有活一日算一日,尤其是有了孩子做羁绊,哪能如未出阁时那般如意自在。这王娘子既同师父投缘,便是自己人,咱们能帮多少是多少;等有了钱,再再多建几个这样的善堂。”
将离边说边想起许久未见的平阳侯夫人斐柔,不知她近来如何了。
“斐柔近来可去观里烧香了?”
琉羽摇头,“来过一次,师父本想与她聊几句但伯府的人催着走。”
高门大院门户森严,她几次上门拜访都不得入,将离惟有叹息:“希望姐姐安好。”
西屋门一开,涌安的娘抬着浑浊的眼往外看,视线飘忽。
将离心一顿,与琉羽对望,瞎了?
琉羽用口型:是啊,我没说过吗?
将离摇头,她小步走近:“大娘,我是涌安的朋友,来看您了。”
“哎,哎,小安子可好?他跟使团出去可回来了?”老太太伸手茫然地抓着,将离握住她枯槁粗糙的手。
“涌安挑了大梁,这一时半会还回不来,您安心在这住着啊。”
老太太一脸喜色:“好,好,小安子有出息就行。我这身老骨头早就该见阎王了,没得连累他。你若见到他,记得帮老婆子带句话,多听将太傅的指点,要记得感恩。当年若不是太傅救了我们母子,我们哪有今日啊。”
将离一时有些缓不过来,“我父亲救了你们?何时?”
“啊!原来您是太傅的公子?!当年涌安爹死了后,他们家里人就把我们母子赶出去了。大雪天,我们无处可去,路上遇见太傅,他真是个大好人!不但给我们母子俩找了住处,还塞了十两银子。后来涌安大了,还提携他进宫当差,我们母子这才过上了太平日子啊。前几年大疫,老婆子差点死了,又多亏了太傅赠药,我才又活了过来。我这条命都是太傅的。只可惜老婆子如今眼也瞎了,腿也残了,只能日夜诵经,为太傅祈福了。”
将离唏嘘,涌安母子同将正言还有这么一段情分。
可既如此,涌安又怎么会为害将正言呢?
他究竟受何人指使?
事情越发扑朔迷离了。
近日无事,将离将琉羽留在了善堂帮慧修,自己则慢悠悠地踏着月光踱步回去。
她的脑子很乱,看似线索增加,实则都是一个个无解的线头,越抽越乱。她要好好想一想,这中间到底还有什么她不知道的隐情。
不知不觉走到了海棠巷,这是梨花巷的后巷,很窄,昏暗无光。
她敲了敲脑袋,怎么走到这来了。
刚想折返,人就被一堵高墙挡住,抵在墙壁上。
“李承昊?”将离皱了皱眉,“你又喝多了?”
“这两日我一直在想,为何是这样?”他垂着头低喃,“为什么呢?子夏?”
将离哭笑不得,这个人喝醉了说话颠三倒四,她完全听不懂,“什么为什么?”
“你闭嘴,不要说话。”他嗡声嗡气,十足霸道,“我要确认一件事。”
将离仰起头望着他,满是不解,“确认什么?”
李承昊一手撑着墙壁一手捏住了她的下巴,“你别动。”
将离还未来得及反应,他的唇便覆了上来,鼻息炽热,酒气冲天。
将离瞪大了眼睛,脑海一片空白。
她死死抵住牙关,方寸大乱,可李承昊今夜像疯了一样痴缠不放,不仅用舌头撬开她的齿关,还长驱直入,吻得霸道又深沉,连一丝喘气的余地都不给她。
她用力推,可宽厚的胸膛像铜墙铁壁,纹丝不动;漫长的吻彷如几世那么长,直至最后的最后,彼此氧气耗尽,她终于获得一线喘息,狠狠咬了李承昊的下唇,推开了他。
“你疯了!”将离不可置信。
李承昊摸着唇,表情如困兽狼狈又痛苦,“你说对了,我疯了。我真是疯了,将不弃!”
世上那么多男女,怎么偏偏就对他动了心?
该死的,他到底给自己下了什么蛊?
“你告诉我,你对我下了什么降头?为何我会起这个心思?旁的人,女子也好,男人也罢,全然不行,唯独对你。唯独只有你!”
他像是入了魔一样,满脑子都是他。
这个人太坏了,不光占据他的心,还毫不客气地出现在不可描述的梦里。
他宽大的双手郑重地捧着将离的脸,犹如对日月星辰发着誓:
“我确定了。是你,独独是你,无关男女。将不弃,我对你动心了。你……”
“你什么你!疯子!”
将离心脏狂跳,猛地推开他,飞也似地逃走。
“我认定你了!你休想逃!”
李承昊的声音回荡在巷子久久不散,像个魔咒让将离魂飞魄散。
他是疯了吗?!
…………
将离一路跑回翠竹轩,三魂丢了七魄。
将不弃从松涛院过来,见她如此慌张,不由得拧眉:“怎么跟见鬼了似的。”
“见鬼了,是见鬼了!”将离脸色煞白,摸了摸胸口,“夜路走多了,果然是见鬼了。将不弃,明日你自己上朝吧。我,我要告假几日。”
“为何?你又做了什么亏心事?”将不弃心一咯噔,“快说!”
将离拎起桌上茶壶,对着壶嘴咕咚咕咚饮了个痛快,才道:“今日我为崔永真求情了。”
“混账!谁让你……”将不弃气得想要站起来捏死她。
“稍安勿躁!”将离白了他一眼,“陛下没有责怪,宽恕了崔永真。不过,我同太子在东宫稍有争执,还是缓几日再见吧。如今大势已定,尚书大人你登阁拜相亦指日可待,难道不想亲自站在朝堂呼风唤雨?”
这句话说到将不弃的心坎上,他的确是这么想,也想试一试。
只是这个腿还站不起来,他犹豫该寻什么借口。
将离斜睨了眼,看穿了他的心思,揶揄道:“陛下如今腿脚亦是不便,你的腿疾,倒是因祸得福。臣子与君同忧,尚书大人又走在了群臣的前端。”
她满嘴阴阳怪气,将不弃有些恼怒,可不好发作,“正好选妃一事我要同太子细细斟酌,那你就歇几日吧。”
他转头离开,诡谲阴毒的笑随即浮上唇角。
若重返朝堂顺利,将离即可杀。
二皇子封在木箱整整七日。
从一开始的抓挠、哀泣渐至无声,直至箱子开始透出腐烂的气味。
这气味如同海滩暴晒九九八十一天的死鱼弥漫整个大殿,绕梁不绝,又钻入每一个入殿议事的朝臣鼻子里,像钝刀子割着肉,一分一秒都是折磨。
秋凉起风,本该爽朗温怡,可朝臣们手持笏板如立于凛冬大雪,脊背发寒。
将不弃坐着轮椅来上朝,皇帝只抬了抬眼皮随口一问,便不再提了。
倒是李承昊愣了半晌,想不明白他怎么又瘸了腿。
退朝后他想问,但将不弃被东宫的人带走了,他只能悻悻作罢。
如此,接连着几日上下朝,除了大殿臭哄哄的,一切皆如常。
将不弃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
众臣皆沉浸在腐朽的死亡之中,一个个灰败着脸,唯独李承昊眉头皱得像山川大岳,沉重而愤懑。
将不弃竟然视他于无物,非但对他的深情凝视毫无反应,竟然像不认识他似的,同他生疏又冷淡。
他这个狗东西!猖狂得志,小人!
李承昊几次想要堵着他,要么是同僚人来人往,他又坐在轮椅上,总觉得隔着距离,不好亲近;要么就是看着他与太子聊得热火朝天。
想起那日在芙蓉山庄将不弃为了救太子几乎丢了半条命,他就像是蔫了的公鸡似的,无精打采。
如此又过了两日,他似乎想通了,又跟打了鸡血似的,开始操练起禁军和殿前司了。
跑马、搏击、射箭、负重奔跑,日日加码,玄晖累得跟狗似的,忍不住为大伙儿求情:“爷,今日可否少跑几圈?”
“你瞧瞧你,来雀都才多久,身子骨就废了。跑起来,今日没跑完二十圈不许吃饭!”
禁军的将士们纷纷打听,总督这是怎么了?
玄晖闷头跑,怎么了?
他怎么知道怎么了!
将离躲在翠竹轩几日,心绪难定,便去善堂找慧修。
师父无所不能,定能给她指一条明道的。
可慧修不在,连琉羽也不在。
今日她依旧一身白色海浪纹箭袖骑马装,但怕被人认出,特地戴了顶斗笠帽,遮阳又挡脸。
刚进善堂,迎面便撞上了王娘子。
她满头都是汗,红光满面的,像是一路小跑而来,见到她一拍大腿:“哟,我正要去找您呢!慧修师父说城郊外东郭村那有个荒废的庙,她想把地买下来,让我赶紧回来,请您去一趟,一块儿参谋参谋呢。”
将离一笑,走到水缸旁,给自己舀了杯水,也给她递了一杯:“师父看好买就是了,没必要我参谋。琉羽呢?”
“琉羽姑娘昨日去乾县了,说是去请什么夫子,给咱们慈幼局的孩子们开蒙讲学呢。”王娘子咕噜咕噜一饮而尽,用袖子擦了擦嘴,“咱们走吧,没得让慧修师父等呢。”
左右也无事,将离点头应承了。
她进屋跟涌安的娘打了个招呼。
涌安的娘本想请她帮个忙去趟梅陇村。
这些年她替涌安攒下不少银子,都偷偷埋在家中那个鸡窝下边,想着善堂和慈幼局都缺钱,眼下又没到娶媳妇的时候,想取些出来给慧修。
可她还没来得及张口,就听得将离跟王娘子走了,只得作罢。
“马车太慢,跟我骑马走。”
将离让王娘子随她上马,一道出城。
城门口,玄晖指着她的身影对李承昊道:“哎,爷,您看那个人像不像将不弃?他腿伤又好了?啧,那个胖娘子是谁?”
李承昊早就看见了,只消背影他都认得这是谁。
他娘的将不弃,嫌弃他也就算了,找个肥婆算怎么个事儿。
他还不如肥婆了?!
他心里气炸了天,有苦说不出:“他要吃屎你管得着么!”
玄晖无端挨了顿骂,挠着头万分委屈:“我没说他吃屎啊。”
东郭村在城郊三十里,策马也就半个时辰。
那破庙在一个村口的半山腰,破是真破,外头都挂蜘蛛网,周遭都是树,安静倒是挺安静的。
“前头有河,下头就是村子,这地方还行。多少银子?”将离背着手跨进庙门,朝里头喊,“师父?”
里头无人响应。她转身想问王娘子,庙门啪地一合。
昏暗的大殿落下一张巨大的网,将她死死网住后,唰唰落下几个蒙面的黑衣人。
“你们是谁?!我师父呢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