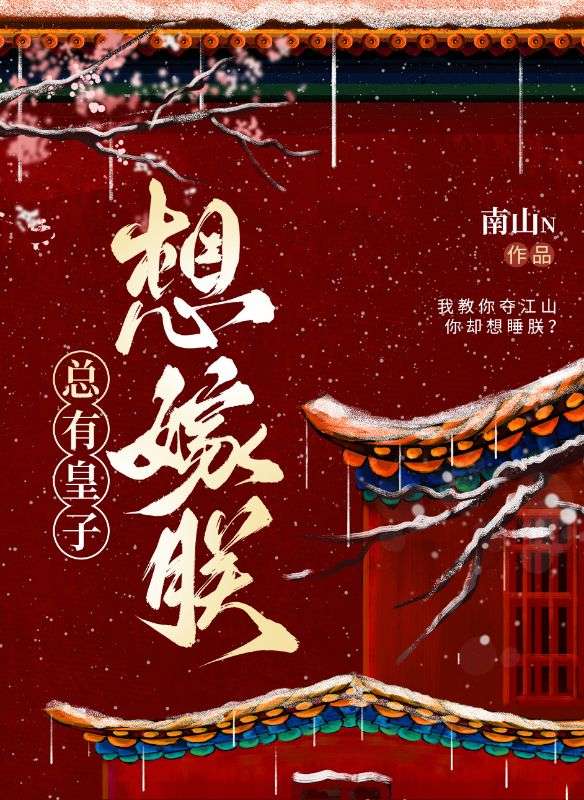
上点众小说APP
体验流畅阅读
第23章
看见
丁长卿的父亲丁越原是礼部尚书,因受卫氏谋反之事牵连被革了职,好在丁家是在三族之外,没有被抄家灭族,算不幸中的大幸。
丁长卿的礼宾司闲差自然也没有了,如今闲赋在家,靠着舒王引荐,本想来东宫寻太子求个差事,没曾想竟然看到如此鲜艳的一幕。
原来传闻中太子和将不弃的关系都是真的啊。
不用猜也知道,定是因为东宫选妃之事,将不弃与太子生了嫌隙。若说男人对男人,没有人比丁长卿更懂了。
他对太子夸下海口,定能让将不弃对太子死心塌地。
太子正懊恼着呢,挥手让人将他赶出去:“去去,你知道个什么!”
丁长卿不死心,偷偷跟在将离身后。
出了东宫就是拱宸门,将离的情绪坏到了极点。
再没有比现在更让她觉得沮丧的了。
孟贺嶂进了京,本以为能从他身上撬开口子,没想到他也是个倒霉蛋,一夕之间家眷被屠戮殆尽,怎么看怎么都不像出卖太傅的人。
再看看太子,不仅怯懦自私,还荒谬绝伦,她更觉得家国无望。
爹啊,大庆,要亡了!还做什么帝师啊。
这一夜她独坐揽月楼,豪掷千金,点了姑娘吹拉弹唱,喝了许多许多的酒。
也不知何时,丁长卿走了进来同她打招呼:“大人,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?”
他是个自来熟,将离同他饮了几次,也算相熟,便招呼他坐下。
“长卿,别来无恙?”
“唷,您这话说的,就差脱一层皮了。”丁长卿闷头一杯。
丁家为了洗脱附逆卫党的嫌疑散尽了家财才得以保住身家性命;他的母亲是卫贵妃的妹妹,深知自己卫氏女身份会牵连丁家,选择了自缢。
覆巢之下,安有完卵?
再看看将家平步青云,说不眼红是假的。
可人家将不弃命好,出身好、长得好;不仅文章做得好好,他妈的武功还高。
救驾之功,这世间可没几个人有这福气呢!
“将大人呐,我太羡慕你了!”
他都羡慕得流口水了。
“我自罚三杯。”将离虽然半醉微醺,但还没全糊涂。
她半仰起头,雪白的天鹅颈透着诱人的光泽,丁长卿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
难怪太子也看上他了,的确是尤物,可比整条梨花巷最好看的小倌儿还要好看。
趁着她举头饮酒,丁长卿在她的酒壶里撒了东西。
“尚书大人,如今您春风得意,若有什么鞍前马后跑腿的差事,也给我介绍介绍?我这实在是活不下去了。”丁长卿拎起酒壶,殷勤地为她倒满。
酒醉迷人眼,将离眼前都出现了重影:“我?我何德何能?你该去求陛下才是。”
“哎,您别谦虚。三代帝师,您可是未来首辅啊。来,我敬您!”
将离醉了:“不提帝师!今日谁提帝师,我跟谁急!”
丁长卿哄着她:“好好,不提,不提。喝!不醉不归!”
“不醉不归!”觥筹交错间,又开了好几坛酒。
席间舒王带着葵娘子也来饮了几盏,闲聊了几句,将离已经醉了七八分了。
梨花巷子外,玄晖买了火烤板栗递给李承昊,“爷,这板栗非得要上这巷子买吗?我记得咱们府门口就有小摊在卖啊。”
李承昊斜睨着他,丢了颗板栗在嘴里嚼着:“板栗,它就得吃这条巷子里烤的才香。你懂不懂啊!”
玄晖撇嘴,转头问崔无咎:“崔公子,真是这样?”
崔无咎磕着板栗摇头晃脑,“有些人啊,吃的是板栗,想的可未必是东西。长煦,我考考你,襄王有意、神女无心,出自何处?”
“呸!”李承昊吐了板栗壳,一脚踹了过去,“出自你的狗嘴,吐不出象牙的东西,还不早点滚回家去。”
“嘁!好心当成驴肝肺啊,我早就同你说了,将不弃高冷孤傲那是全雀都出了名的。你说他对你热情,我看全都是装出来的。他就是利用你。”
崔无咎站累了,随地找了个门槛石坐了下来,边说还边招呼玄晖统一战线:“阿晖,你说是不是?”
玄晖可不敢乱说话,胡乱塞了几颗板栗进嘴里装死。
李承昊憋着一肚子气没地儿撒,眼睛不自觉地往揽月楼看,二楼包间开着窗一览无余,丁长卿的手都摸上了将不弃的手背了。
“你们懂什么!他怎么不利用你?不利用别人,偏就利用我?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与众不同。”
李承昊一脚踢掉脚步的小石子,砰的一声,石头冲出去老远,砸到了一个过路人的脑袋。
那人惨叫了声摸了摸脑袋,破口大骂:“哪个王八蛋打我?滚出来!”
崔无咎一脸同情地看着玄晖:“你家主子脑袋坏了。”
“长煦,这是病,得治!”
李承昊捏着拳头作势要揍他,吓得他扔掉板栗,转眼逃得没影儿了。
那头,将离在揽月楼小厮的搀扶下,上了丁长卿的马车。
“尚书大人慢着点,我送您归家去啊!”
“哎,这不是长煦吗?”丁长卿看到他,远远打了个招呼。
将离醉眼朦胧没有回头,李承昊扭头就走。
玄晖三步并两步跑到前头巷口解开马缰绳,拉出两匹马,“尚书大人也是,一个人喝那么多,连个长随都没带。”
李承昊翻身上马,刚跑出去几步又调转头,对玄晖道:“你先回去。”
玄晖一脸茫然,“您呢?”
李承昊没搭理他,自顾自策划往丁长卿的马车后追了出去。
马车走得很急,转眼即没影了。
李承昊勉强顺着地上的车辙,朝城南追了过去。
玄晖一路跟了上来,“爷,这方向不对啊。”
“当然不对!丁长卿这个狗崽子!走!”
就知道他没好心!这厮好男风是雀都出了名的。
两人赶到城南一个偏僻的农庄外,果然,外头停着丁长卿的马车,车夫不知跑到何处去了。
李承昊一脚踢破木门,丁长卿这个狗东西正在解将离的扣子。
长鞭如毒蛇吐信,打得他嗷嗷直叫:“总督,我和将大人你情我愿的事,你这是做什么?!”
“你情我愿?”李承昊又狠狠抽了几鞭,“你要不要撒泡尿照照自己?!”
他娘的,他堂堂北冥世子,一表人才、风流倜傥、潇洒不羁将不弃都没看上,会看上这肥猪一样的丁长卿?!
简陋的木板床上,将离面色潮红,眼半睁半阖;微敞的领口白肌似雪,直让人挪不开眼睛。
“你喂他吃什么了?!”李承昊牙根发痒。
“就就五石散,助助兴的。我冤枉啊!”
李承昊气得又抽了几遍,对玄晖道,“他身上定还有,喂他吃,吃完了扔猪圈去!”
“总督,总督饶命啊!”丁长卿吓得屁滚尿流,如竹筒倒豆子一般倒了个干净,“我这么做,不是为我自己,是为了太子殿下啊!”
“太子殿下喜欢尚书大人,他俩蜜里调油,是太子殿下让我给大人下点助兴药的,大人,同我无关呐!”
丁长卿将自己推得一干二净。
他本是准备把人往东宫里送的,可半道上实在是受不住这诱惑,想自己先开开荤,这才把人带到城南的庄子里。
李承昊懒得同他废话,将离在朝他看呢。
他小跑到榻前,用披风将她裹上,打横抱了出去。
将离似醒微醒,纤细的手指轻轻抚上李承昊的眉心,声音又酥又麻:“长煦?”
“是。”李承昊咬着牙,托着她朝身上抻了抻,“喝了多少?跟死猪一样沉。”
呵,将离淡淡地笑了笑,眉心却依旧紧蹙,只是脸朝着他的胸膛蹭了蹭:“你看见我了?”
李承昊带她翻身上马,拉着马缰绳。
将离正对着他跨坐,半个身躯靠着他,没有了白日的冷漠,披风下的她又瘦又小巧,像只黏人又可怜的猫。
李承昊心都软了,哪还有半点气,他低下头看着怀里的人,既无奈又哀怨:“想要看不见你,很难。”
“你怎知你看见的我,是我?”将离的手按在他厚实的胸膛,撑着脸仰头看他。
那双眼睛裹着浓重的酒意,连眼尾都在勾人心魄。
这个妖孽,又想要趁着夜色为非作歹了。
李承昊强压着腹部的燥意,咬牙切齿:“你化成灰,我都认得!”
将离嘟着嘴,委屈地摇着头,“你骗人,化成灰如何还能认得。你们都在骗人。我爹也骗人。”
提及太傅,她又低下头呜咽地啜泣着。
李承昊揽着她,轻拍了拍后背,声音低到尘埃:“我送你回家。”
将离揪着他胸前的衣襟,疯狂摇头:“我不回去,那不是我的家。”
她挣扎着想要从马上跃下,惊得李承昊收紧缰绳,勒马停了下来,强健有力的手臂将她牢牢圈在怀中,稳如泰山。
“你想去哪?”他的声音似乎从遥远的银河飘来,磁性又醇厚,低低地呢喃,勾着她的渴望。
五石散在酒的催发之下快速起效,将离伸手圈住李承昊的脖颈,抬着流萤般的眸子痴痴地看着他,声如午夜魅魔:“敢不敢带我回家?我要让你看到我。”
李承昊的薄唇被她鼻息呼出来的热气吹得发颤,声音如堵了棉花在喉间打转,手不自觉地攥着马缰绳开始僵硬,人都变得无比笨拙。
他好气!怎么三言两语又败下了阵。
一想到这,他粗起嗓子恶狠狠回道:“敢,怎么不敢。”
秋末的夜风很凉,马蹄疾驰在黑暗中,两人的心跳逐渐同步。
她的手很凉,挂在脖上却烫得如同烙铁,李承昊几乎是飞回了总督府,连马都顾不上圈,抱着她就往寝房跑。
这个将不弃太坏太坏了。
他绝对不能这么算了!
他恶狠狠地将人扔到床榻上,手指颤抖:“狗东西,你又想玩什么把戏?有什么招都给爷使出来,爷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坐怀不乱!如今我剑术已成、道心坚定,绝不会再上你的当!”
将离的帽子都被甩掉了,发髻松散,黑发垂肩如缎;两颊成了桃花面,眸中春色无边。
她只是轻咬了下唇喊疼,李承昊登时恨不得扇自己两耳光。
“罢了罢了!妖孽!”他恨死自己了。
全然斗不过这个妖精!
打不过,只能跑了!
他转身拉开大门,将离低低耻笑:“原来你不敢。”
砰!李承昊狠狠合上门,顺势还插上门栓,气得头发都炸了。
“我警告你!别以为爷不敢动你!你再这么看着我试试!”
将离从床榻起身,一步一步朝他走过去,唇角浮动冷笑,黑眸在烨烨烛火下逐渐变得癫狂:
“崔无咎不是会剖尸验骨吗?他有没有告诉你,人褪去皮囊有二百零六骨,可披上人皮,确有一万八千相。你是何相,我是何相?你眼中的我又是何相?”
她突然开始倒书袋念佛偈,李承昊虽满头雾水,可还是迎头直视毫不退却,“任你皮囊千万张,我也认得你。旁人都是二百零六骨,你多一块,脑后反骨。你这个黑心肝的,走到哪、幻成何相,我都认得你!”
将离眼圈微红:“我黑心肝?你剖过?我也许无心呢!”
“无心?”李承昊气不打一处来,伸手开始撕她衣裳领口,哧啦一声,玉石扣子掉落在地上,砰地在地上打转,又顺着地面不知溜向何方。
“好啊,取刀来,让爷剖开来瞧瞧,到底是黑心,还是无心!耍我有瘾是吧!”
将离目光挑衅:“来。不敢是小狗。”
“他娘的!”李承昊头一昏,两人互相扯起了衣裳,很快,外袍落尽,两人都剩下一身雪白的交领里衣。
李承昊死死握住她的手,眸光坚定如昨:
“我敢。你敢吗?废物点心,只会躲。”
“我不躲。我要让你看见我,真正的我。”
将离甩开他的手,迎着他炽热的目光,解开腰带、撩开里衣,胸前层层捆扎的白布让李承昊彻底呆如木鸡。
他像一个雕像矗立在将离面前,连呼吸都滞住了。
将离仰着头,一层层松开棉布,长长的布条一圈圈地垂在地上,犹如层层剥开的洋葱,秘密就这样猝不及防又一丝不挂地展露在李承昊的面前,让他从极冰之地飞跃至火山之巅。
他的耳畔有声音如潮水涌来:
“我,不是将不弃,我叫将离。看到了吗,这才是我。我,叫将离。”
泪决了堤,委屈无所遁形。
坚硬的外壳之下裹着一个小女孩渴望被光照耀的怯懦。
她抽了抽鼻子,故意挑衅他:“看清了?!滚吧!”
“滚你大爷!”滚烫又粗糙的大手掐着她的腰,一把举起她,将她扛在肩上;
没等她反应,整个人又被甩在柔软的床榻上。
那道厚实的身影根本不给她反抗的机会,如高墙颓塌,死死压了上来。
“该死!该死!我早该想到的!”
那相同的脸,相似的眉眼;一个寡淡无趣,一个让他如痴如狂。
大手拨开将离额间的乱发,李承昊疯了似地吻她,失而复得、欣喜若狂。
粗哑的嗓不停地喊着她的名字,“你是将离!将离!”
“是,我是将离!”她的泪顺着眼角落在锦被,开出了一朵朵绚丽的花。
吻到彼此都耗尽力气,李承昊眼眶濡湿,深情又缠绵地望着她,眼里拉出长长的丝线,一圈圈将彼此绕在一起。
将离醉意缭绕,再度伸手圈住他的脖子,将他的头拉向自己,在他的耳畔吹着热气:“怕了吗?”
“怕你爹。”粗哑的嗓,温柔得不像话。
大手刻意抬高她的下巴,霸道又缠绵地覆上她的唇,直吻得天昏地暗、日月无光。
热浪拍打着礁石,又激起千堆雪,他们在浪潮中紧紧相拥,再也不是天地的孤鸿。鹤鸣九皋、鹰逐长空,朝阳和路匍匐在他们的脚下;山河蜿蜒,欢乐奔腾地向着未知却映着绚烂天光的尽头。
“可以吗?”他低低地在将离的耳畔呢喃,像一个巨大的熔炉,要将她融化。
她热得透不过气,翻身在上,学着他捏着下巴,“求我。”
他俊朗的眉眼噙着笑,半坐起,双手掐着她的腰,如蜻蜓点水似的,亲着她额头、鼻尖,红唇,一点一点向下:“求求了。”
他学她的语气学得极像,将离笑了,“孺子,可教也。”
得到许可和赞美,他浑身爆发无穷无尽地力量,一个翻身又将她锢在身下。
再没有过多的语言,他们在天地之间见证彼此最真实的一面。
疼痛如凤凰涅槃,枯骨一寸一寸长出血肉。
她抬手描着李承昊的眉眼,低声呢喃:
“若非有你,我本无相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