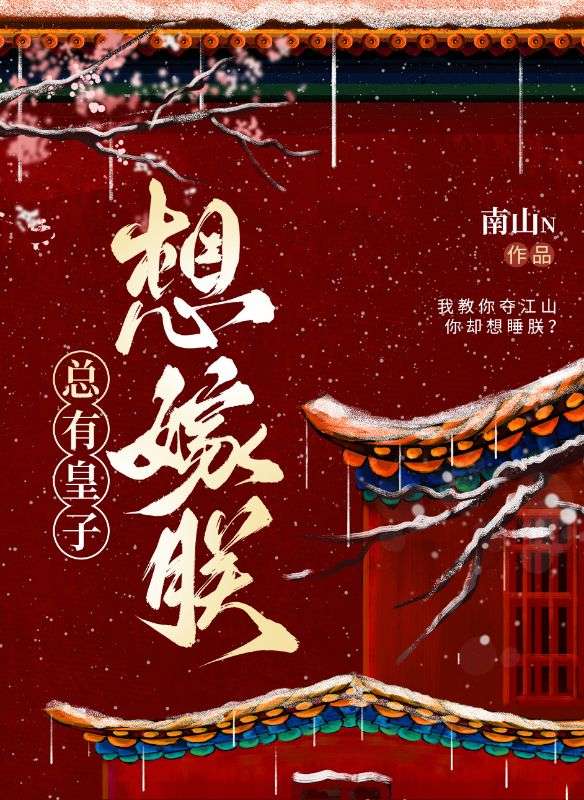
上点众小说APP
体验流畅阅读
第18章
救驾
将离心急火燎赶去流星阁。
卫家敢烧死皇帝,就更不会放过储君,太子危矣!
垂云大殿通往流星阁需要经过一条绿萝小道,两侧横七竖八躺着不少尸体,将离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天杀的,太子要是死了,这帝师也做到头了。
两侧灌木丛似有人头晃动,将离蜻蜓点水一跃而起,揪住那脑袋上的头发就往道上一甩,竟是将之瑶。
她摔得四仰八叉,见是将离,恨得咬牙切齿:“他们都死了,你怎么没死?”
“你都没死,我怎么好意思先死!”将离懒得理她,拔腿就走。
将之瑶扑过来拖住大腿,“太子哥哥被坏人绑了,都是你这个灾星害的。你不许走!”
将离蹬脚,愣是没蹬开她,怒火上头,“你再拖着我,太子人头落地,你这辈子休想当太子妃!”
将之瑶攥住她的袍角不撒手:“你带上我。”
将离像提小鸡一样将她拎起来,“能不能走?不能走别碍事。”
将之瑶对太子的确上心,一瘸一拐走在前边带路:“能,我要救太子哥哥。”
这种时候怎么好让将离一个人出风头,她必须在。
将离眉头紧蹙:“几个人?”
“两个。”将之瑶举着双手,默默比了个剪刀,改了口。
将离嗤了嗤,不足为惧。
流星阁鸦寂无声,东宫伺候的太监婢女尸首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之中,大殿门口由两个黑衣人把守。
将离小心翼翼靠近,寒光一闪,两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倒下,她低声对身后的将之瑶叮嘱道:“待外头别动,我去把太子带出来!”
她一踹门,殿内灯火通明,乌泱泱的人头看向她。
至少十七八个人,将之瑶这坑货!
领头的正持剑逼太子写着什么文书,东宫长随天禄浑身血淋淋跪在地上,两个黑衣人押着他的双手,一人正高举大刀要砍他的脑袋。
将离想也不想掷剑而去,正中那手举大刀的黑衣人胸口,她一个鹞子翻身冲了过去,在黑衣人倒下之前拔出了剑,反手一挥,斩断另一个黑衣人的脖颈。
天禄没了束缚,低头拾剑,与围拥而来的黑衣人展开厮杀。
太子身侧领头的黑衣人一看架势不对,索性也不要什么文书,直接挥刀想杀死太子了事,说时迟那时快,寒刀只差须臾就要砍断太子脖颈,将离挑剑一抵,刀刃相接迸裂火星;太子脖颈一寒,发丝断了几截,飘飘洒洒、失魂落魄,骨头酥软,重重跌落在地上。
只差一点,只差一点呐!
他摸着自己的脖子,看着将离与四五个黑衣人厮杀在一起,惶恐惊惧地向后退坐了好几步:“阿离,小心!”
有黑衣人朝太子砍去,将离飞身而上,扑了过去,护住了太子,自己却被砍中了手臂。“殿下,你快走!”
“天禄!带太子先走!”将离大喝。
天禄杀红了眼,“是!”
太子躲在天禄身后,步步往门外退,“阿离,你小心呐!!”
将之瑶不知何时偷偷摸到门口:“殿下,快跑!”
天禄护着太子退出大殿,将之瑶眼珠子一转,撕开衣角将大殿门用布条捆得死死的。
里面的黑衣人无论如何撞,都打不开门。
“好啊!都是你坏了我们的好事!”
他们将怒火全部指向了将离。
将离啐了口唾沫,没有废话挥剑而上。
这些人都是高手,招招凌厉,出手就是绝杀且人数众多,如车轮反复进攻,将离力有不逮,手臂被划破了好几道血口子。
他娘的,将离怒骂了声,扯破衣角当布条将手与刀绑死,再度陷入血战。
李承昊循着踪迹追来流星阁,踢开大殿的门,看到的是极其惨烈的一幕。
将离握剑单膝跪地,满是豁口的剑笔直插在地上成了她的支柱,瘦削的身姿摇摇欲坠,一袭白袍血染成梅,满脸都是未干的血迹。
长睫微微一抖,两滴血如泪滑落,她的唇轻颤,却发不出声音。
黑衣杀手的尸体如天女散花般倒在地上,血流成河;已分不清哪些是黑衣人的血,哪些是将离的血。
她就像是从血之湖泊中傲然而生的白莲,妖冶又空灵。
天地皆浊,唯她独清。
“他娘的!”李承昊像是被重物撞击,心如佛钟回荡嗡嗡,脑海一片空白。
他惊慌地冲过来,又气又恨,“为了个太子,你不要命了!”
“我,强得可怕。”将离吁了口气,手指蜷成拳死死握着剑,松都松不开。
李承昊解开她手上的布条,将她的手指一个一个掰开,剑咣当落在地上,手已经僵硬蜷曲。
他把将离的手放在手心来回揉搓,仔仔细细为她松弛筋骨,可她身上的伤太多了,手臂、背部、腿部,刀口虽浅,但渗出的血染红了衣裳,小脸苍白如纸。
李承昊一把打横抱起她往外走,边走边呲:“是是是,你最强。天下第一强,行了吧,侍郎大人。没死算你走运,这帮人可都是卫家重金豢养的死士。”
他的怀抱很烫,靠着很安定,将离浮唇轻轻一笑,没有力气接话;她似乎走了很长很长的路,已经精疲力尽了。
李承昊将他抱回大殿空地,双庆在人群中翘首以盼,见到她满身是血呆了呆,立刻迎上去。
“照顾好你家公子!”李承昊斜睨了一眼,确定双庆搀扶好她之后才转头离开。
他身为禁军总督,还有很多事要善后。
双庆一步步搀着她回房:“您这是怎么了?怎么伤成这样?”
“将之瑶在哪?”将离问,瞧见非掐死她不可。
“二小姐在前头偏殿陪着太子,今夜好险,听说宫变了。”
将离浑身像散了架,“去倒水来,我洗洗。”
双庆哎了身退了下去。
将离就直接瘫倒在地上,从袖中摸出那封信。
信口封着蜡泥还印着太傅将正言的私章,并未被拆封过。
将离展开信,熟悉而遒劲的字体迎面而来,是将正言写给北冥王李长白的。
北冥王亲启,
叶州至凉州大营约二百里,吾与使团寅时出发,巳时三刻可抵达。
州与州之间山路多崎,天热,团中有人难耐暑气,怏怏未愈;
私以为,使团抵凉后暂歇二日再启程去锡国为宜。
炼火熬油慢驱慢行,若有叨扰之处,望望王爷见谅。
铁骑无需过早至鸣沙山坳口,以免徒晒劳累。
……
将离噌地坐了起来,屏住了呼吸。
叶州私炼铁!
将正言用的是藏头诗的写法。
他想偷偷告诉北冥王,这么说,叶州刺史屠光要反?
父亲的死,难道是叶州刺史干的?!
可恶,此人事发后痛哭流涕如丧考妣,她和朝廷都被屠光骗过了!
她迅速看下去:
另有寥寥数语乃思亲之故附于信后,望王爷转达吾儿。
父遥望明月昭昭,思苍生疾苦辗转难眠;
登州大旱颗粒无收,民易子而食;巴州山洪大涝,房屋瓦舍皆随浊流覆灭,死伤无数;民无寸瓦、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,天灾乎?人灾乎?
西山有神龟,北岳出螭虎,山崩地陷,异象频出;星坠木鸣、国人皆恐。节度拥兵自立,百姓如浪而逐,国有分崩离析之势。嗟呼!
世道乱而仁义崩,政出其令而无人尊,吾为帝师上愧天子,下愧黎民。楛耕伤稼、政险失民;为帝之师,需知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,非一人之天下。
吾儿入仕当心怀悲悯、肩挑苍生,居庙堂之高不忘民之根本,辅天子施仁政以慰百姓疾苦;君不仁臣不敬则民不聊生,帝师当涤其心、濯其足,时时劝诫、警醒,心常怀忧。千人诺诺,不如一士谔谔。
惟望吾儿肩挑日月,筚路蓝缕、以启山林。
非千万人吾往矣!
昭昭云端月,此意寄昭昭。
……
明月昭昭。
这封信重复了几次昭昭……
像是将正言特地写给她的?
将离读完已是泪流满面。
只是,父亲怎会猜到,有朝一日她会入朝议政做帝师呢?
一个谜团解开,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谜团。
这场宫变来得遽然,却又并非毫无征兆。
皇城司使谢世忠以戴罪之身迅速查清了整个案情。
贵妃为了二皇子联合卫家密谋在避暑山庄对皇帝动手,事发前她端了一碗放蒙汗药的参汤,迷晕了皇帝。
卫子廊作为内应,假借负责安防之便,悄悄放死士入岛;他们本想借着月黑风高夜快速占领芙蓉山庄,诛杀太子,逼皇帝改立二皇子为储君,可没想到垂云大殿竟烧起来了。
火烧大殿的又是另一帮人。
北冥战事不断,各项军需资费陡增,地方灾乱频生,处处都在要钱;可国库这些年早被占据六部要职的雀都世家一点点掏空了,根本没什么钱。
窟窿越来越大,账目填不平,就无法应对皇帝问询。
工部文户部一合计,不妨就烧了垂云殿,再以修缮为名虚增费用,糊涂账糊涂办,事后大家都能安枕无忧了。
纵火时,谁都不知道皇帝在大殿里面。
放火这件事吃力不讨好,就交给寒门出身的汤宪来办。
火是他放的,这锅也当然得由他来背。
汤宪百口莫辩:“陛下,老臣冤枉啊!老臣忠心耿耿,这件事是文大人他们……”
工部尚书文若承直接打断他的话,“陛下,汤宪竟敢火烧大殿,这是弑君啊!他目无君父、贪腐作乱,理当五马分尸!”
堂下有利益牵连的大臣纷纷附议。
皇帝心里头明镜儿似的,户部的窟窿不是一日两日了,这帮人是拿着汤宪的命来平账呢。但火是他放的,的确该死。
汤宪这把刀,最终捅向了自己。
皇帝当场诛杀汤宪;文若承、颜直等因督办不利连降三级;而将不弃有救驾之功,不但未被牵连,反而当场擢升为户部尚书。
李承昊松了一口气。
没想到工部的人玩这么大。
他们本来只想弄塌个亭台楼阁让汤宪贪腐工程款的事曝一曝,没想到他自己把自己点炸了。
不得不说,卧龙凤雏,得之可断腿。
没错,皇帝的腿断了。
贵妃被废赐鸩酒;卫子廊凌迟;卫氏夷三族;
二皇子跪在殿中痛哭流涕,直说谋反案与自己无关。但这一次的眼泪再也打动不了皇帝了,他召了人抬进一个木箱,当着满朝文武的面:
“把这逆子关入木箱不得喂食喂水!”
“父皇,父皇!儿臣冤枉啊!父皇!”
二皇子被塞入狭小的木箱,身子只能蜷缩着,不停在箱子内叩着木板。
太后在珠帘后幽幽一颤,哼,这算是杀鸡儆猴吗。
卫氏真是不中用,搭了台子让他们唱戏也唱不成,废物。
“皇帝,虎毒尚不食子,赐他一杯毒酒便是,何苦如此?”
皇帝断了腿后他性情大变,像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,全然不想做面上功夫,眼神阴鸷而狠厉:“朕往日的心慈,皆成了人尽可欺的怯懦。朕还没死,有觊觎江山者,当如此子!”
满朝文武皆跪地,萧相高冷,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;有几个德高望重的老臣实在不忍,出列求情,其中就有国子监祭酒崔永真。
“陛下,君仁,莫不仁;君义,莫不义;君正,莫不正。一正君而国定,君不乡道,不致于仁,只会徒增百姓恐惧,与夏桀何异!”
皇帝大怒:“放肆!崔卿之见,难不成子弑父,还是父之过了?你真是迂腐过了头,枉读圣贤书!”
“子弑父天地不容,可您如此残暴对待儿子,定会被世人诟病!臣叩请陛下将此子交由三司,依大庆律法严惩!”
老臣叩首:“陛下!三思啊!”
“好好好!你们都和朕作对!你们忠的到底是他,还是朕?!”皇帝失去了理智,“那就都跪在此处,看着这个逆子断气!没有朕的允许,不得起身!”
皇帝拂袖而去,满朝文武战战兢兢。
几个老臣就这样对着木箱跪着,听着二皇子在箱子里发出的哀鸣,面露恻隐和不忍。
太子躬身来到崔永真身旁,心有余悸:“崔大人,您少说两句吧。”
“太子殿下,二皇子乃你手足之情,纵然他该死,也不该如此受折磨,此非人伦亦非国法,而是暴政、恶行。请太子殿下去求陛下收回成命吧!”
太子惊惧地向后退:“崔大人,你这不是为难孤么。”
崔永真欲再说些什么,可最终还是失望地闭上了眼睛。
将离对着他挺直的脊梁躬身行礼,“崔大人切勿动怒,晚辈去劝。”
李承昊轻轻扯动她的袖袍,示意她出大殿。
“陛下正在气头上,缓缓再谏。”
将离颔首,抬眸恰巧与他目光相交,两人不约而同又错开视线,都有些不自在。
自芙蓉山庄回到雀都后,两人这是头一次得空私聊。
李承昊护驾有功,陛下将让他从原先的禁军都指挥使兼管殿前司都指挥使,忙得飞起。
将正言书信中所述的叶州私炼铁之事干系甚大,两人商量后决定暂时不向朝廷举发,私下飞鸽传书北冥核实。
师爷孟贺嶂已启程进京了,此刻急也无用,只能等见到人再细问了。
“你……还好吧?”将离想起那日在火中,他多次被掉落的木头砸到,事后也没来得及问他伤势。
而比起身体的伤,更折磨人的,还有流言。
雀都不知从何处传出风声,废妃卫氏和二皇子铤而走险谋逆,是因为李承昊的身世。
传言李承昊是陛下与已故北冥王妃的私生子,陛下甚至有意立他为储君。
流言四起,如投石落湖,很快就扩散出去,酒楼瓦肆说书的唾沫子横飞,像是各个都亲围在床头见证过这段不堪的情事。
大街小巷的话本子都出了好几个版本了。
李承昊敛眸默不作声,他大体知道将离想要问的是什么,可他并不在乎。
他在乎的是另一件事,“你小时候可曾……”
救过一个孩子,给过他铜钱和棉衣?
他还没来得及问,东宫的人就来请将离去议事了。
将离拱手道别,李承昊只能把疑问又咽回肚子。
往宫外走时,他又不自觉回头看将离的背影,疑惑在心头越滚越大,像是巨石,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“玄晖,你说,昭昭有没有可能是个男的?”
他有些难以启齿,可此刻他很希望是如此。
毕竟四五岁的孩子,男女都长得挺圆乎。
“那……不能吧?”玄晖似乎看穿了什么,“爷,属下觉得,昭昭是男是女不重要,重要的是,将侍郎……哦不,是将尚书是男的。您是不是对他有意思?”
李承昊像是听到天方夜谭似的,捧腹大笑,直笑弯了腰,手指着玄晖:
“你在说什么胡话呢!简直笑死人了!我,李承昊,我会喜欢他?天下那么多美女我找谁不行,非要挑个男人!滚一边儿去,再让我听到这话,打爆你的狗头。”
他骂完怒气冲冲管自己走了,独留玄晖一人在风中凌乱。
“我不过是随口一问罢了,那么大反应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