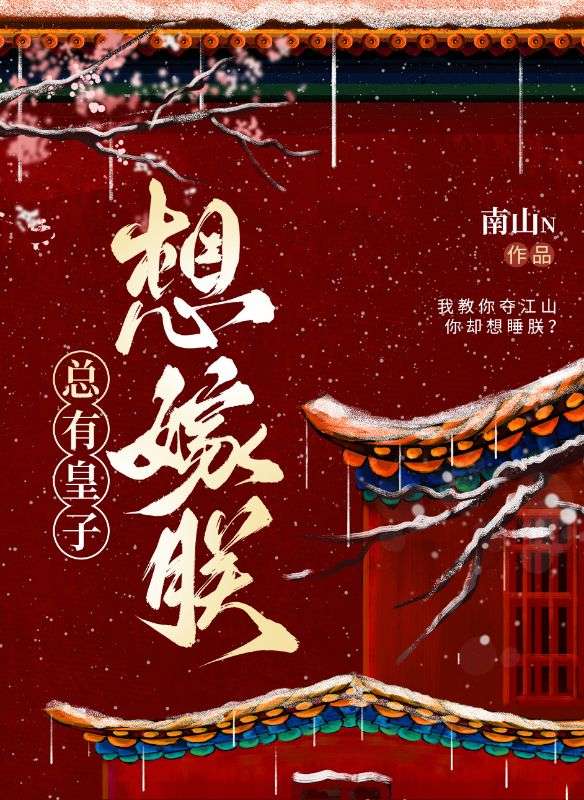
上点众小说APP
体验流畅阅读
第13章
疯狗
秋波如水,那双眼睛重叠合一,他起了幻觉,心狂跳不止。
“眉目含情。”将离抵扇点在他的眉心,慢慢顺着鼻梁滑至薄唇,扇骨轻敲她咬过的下巴伤痕处,哂笑:“总督,发春了?”
舒王等人哄堂大笑:“子夏说得极是。这臭小子就是床榻缺个人。”
李承昊星眸半弯,唇角微微上挑,许是为了看清楚,他的头凑得更近了些,几乎与她要额头相抵,醇厚的嗓子饮了酒,愈加沙哑:“日日夜夜,可想着你呢。”
“想着怎么弄死我?”将离微微仰头,浅唇没有擦口脂,吐气如兰:“那可真是难为你了。”
李承昊轻敛了敛眼皮,抬手捏着将离的下巴,又不客气地滑至纤细而润白的脖颈,皮肤丝滑如缎,手感极好。
灯下看她的眼睛,极像,双眸如星,清澈见底;烛火倒映在双眸,浮光掠金,极美,极魅,几乎让人只对望一眼就顷刻陷落进去,甘之如饴。
可惜是男人。
这不是他的小乞丐。
话说回来,到底是京城的水养人,连男人的皮肤也如此细腻。
“太瘦,养肥了再杀。”
他有些燥热,坐了回去,一口饮尽杯中酒。
将离后颈重量一松,暗自吁了口气。
她轻拉扇面,不疾不徐地扇走脸色的热气,朝李承昊举盏:“等你。”
“别急啊。等爷爷我的不止你一个。”李承昊又恢复了混不吝,朝着左右两侧服侍的女子努了努嘴,“排着队呢。”
“听闻世子一夜御数女,怎么着,如今廉颇老矣,得挨个儿来了?”将离举盏,朝隔壁的谢世钟敬了敬,连一丝眼尾都没有丢给李承昊。
谢世忠干笑,舒王憋着笑,丁长卿看好戏,都不吱声。
“怪留意我的。难不成想自荐枕席?”李承昊朝她挑眉,顺道伸舌将身侧女子递来的葡萄卷进口中,极尽风流。
“糙汉不合我胃口。”将离诛心:“我挑食,不是什么死鱼烂虾都吃的。”
李承昊蓦地想起那日偏院屏风后的女人,哼了声,没反驳。
舒王生怕两人又打起来,出声圆场:
“都是兄弟,喝了这杯酒,翻篇不提了。过几日陛下要去芙蓉山庄避暑,到时候咱们哥几个都去凑凑热闹。这雀都跟个火炉似的,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”
陈长卿扯着领口衣裳晃了晃,他很肥,最怕热了:“我都快烤熟了,这日头太毒,秋后老虎。”
“同去,回头我给大伙儿整点好东西。”舒王朝李承昊眨巴了下眼睛。
李承昊嗡声:“你眼珠子抽筋了?”
“户部事多繁杂,各位大人去吧,我脱不开身。”将离推辞。
避暑这福利,怎么着也该户部尚书颜直去,轮不上他这个侍郎;再者说,“吃瓜、打猎、泡温泉”是常规避暑三件套,前二好说,泡温泉露馅儿的几率太高了。
“没机会都要制造机会踩着旁人往陛下跟前凑,怎么有机会露脸反而推三阻四了?子夏真是好手段呐,欲擒故纵这手绝活,给你玩透了。”
李承昊又斜躺下去,翘起了二郎腿,捶腿、捏肩、喂水果都有人伺候着,舒坦得要死。
将离最瞧不惯这浪荡样,轻嗤:“比不得总督逍遥,这般舍不得我?连激将法都使出来了。”
李承昊食指中指一并,从自己的眼角挥向将离:
“那是。你可是爷爷我放在心尖上的人,不看紧些,怎么行?”
“你的心尖?”将离捏着酒盏笑:“刀尖吧。”
柔荑如兰竹白皙修长,指尖粉嫩,修得圆润干净,精致和讲究刻进了骨子里,难怪让挑剔的舒王都心动了。
李承昊举杯,隔空与她敬了敬,饮了个干干净净:“走两步,试试不就知道了?”
将离轻摇着扇:“走不走,得看我心情。”
都是混迹官场的人,面子里子就如同窗户纸,虽薄,也得将就着糊好。
两人针尖对麦芒斗了几句嘴后便埋头喝酒,饮到最后也算是宾主尽欢。
李承昊酒过半酣就阖眼斜卧,也不知是假寐还是真睡着了。
云淡月昏,已近亥时。
舒王醉了先行一步,谢世忠和丁长卿也默契地告辞,将离起身走出云天楼,小厮去牵马,她持扇立在丹墀上,纱灯落下温柔的光,身形修长如鹤。
一道暗影从背后压迫上来,后颈一沉。
“我同你没那么熟吧?”
将离尝试拨开李承昊粗壮的手臂,纹丝不动。
再拨,他反倒下压得更重,纯纯故意,将离脚下使力稳住身形:“想埋我,光这么压可不够。”
“打个巴掌再给颗枣,雀都人训狗真有一套。”李承昊歪着头斜睨,入眼就是纤细的一抹白,“得意了?”
将离转身用紫竹扇抵着他宽阔的胸膛,唇角噙笑:“你对自己的定位,倒是挺精准的。”
“呵。”锐利的黑眸似笑非笑,眼底是千年的寒冰,“谈谈?”
“想灭口啊?”浓重的杀意裹着酒气,燥热而浓烈,将离挥扇轻摇,“走,也好死个明白。”
李承昊嗤了嗤,勾肩搭背带着她向前走:“没法子,谁让我心善呢。有人上赶着投胎,爷爷我也只能辛苦些,送他一程了。”
“哦,想好说辞了?”将离笑了笑,“说来听听。”
李承昊的大手像摸狗似的,摸上了将离的璞头帽:“简单。就说将侍郎诬陷忠良、良心不安,自绝谢罪。哦……不对,侍郎的良心都让狗吃了,哪还有呢?”
“你吃了?难怪我今儿摸了摸,没找着呢。”将离垂眸笑,“嗯……倒不如说侍郎饮醉了酒,提着灯笼找良心不慎落水来得巧妙。”
“到底是读书人。”李承昊捞着她脑袋压到自己唇边,“一肚子墨水,心肝脾肺肾都是黑的。”
他的声音因为醉酒更哑了,像是喉头堵着棉花打着转,鼻息的热气吹得将离的脖子发痒,她偏了偏头,醉意让她的眉眼全是钩子:“剖开给你瞧瞧?”
“多麻烦。爷是糙汉,喜欢直接杀。”李承昊横了眼牵着马的随从双庆,朗声:“马给我,回去告诉府里,侍郎今夜与我秉烛夜饮相谈甚欢,不回了。”
双庆哪见过如此面恶的人,呆呆地牵着马缰绳,犹豫要不要拉上将离就跑。
琉羽想跟上,将离摆手:“去吧,同家里说,我晚些回。”
李承昊大手一捞,挟裹着她的腰翻身上马,攥了攥缰绳:“坐稳了。”
鞭声清脆,马蹄疾驰在灯火阑珊的街巷,朝城门去。
“打马出城?”将离星眸深了深,“嫌参你的折子不够厚。”
城门酉时关闭后要到次日寅时才开,期间无诏令一律不得进出,李承昊身份特殊,更应该谨慎行事。
将离不由得对他的可用性多了一层质疑。
本以为他看似纨绔、心中藏有沟壑;看来这沟壑生错地方,怕是脑子有坑。
“子夏可真关心我啊。”李承昊阴阳怪气地抽了抽马鞭,有些发狠。
“昭昭。”
风带起衣角,她顿时心情转好。
今夜醉了酒,她看着李承昊突然想起一个故人。
那个哆哆嗦嗦冻红了鼻子,还大言不惭要仗剑天涯、浪迹江湖的少年。
彼时她正在人生至暗时刻,看见他捏着拳头振臂高呼,像极了一道光。
他甚至连一把剑都没有,还叫嚣着仗剑江湖。
将离把身上所有的铜板都给了他:“拿去,买剑。”
那个少年如今应该带着剑,肆意江湖了吧。
想起他,将离唇角上扬,怎么也压不住。
只可惜李承昊只顾着纵马,没有看见她脸上的笑容,风太大,他甚至听不见她说的话:“你说什么?”
将离抓紧了鬃毛防着自己掉下去,“没什么。慢点!”
策马让李承昊有了回到北冥草原的畅快,他提高了速度,笑声在夜空肆意又激扬,所有的压抑和无力瞬间释放,“男儿当如疾风。”
疾风骤停,在城门口差点刹不住。
“何人?”守城将士交叉了矛,挡在马前。
李承昊掏出令牌:“禁军和户部侍郎协同办案,开门。”
“是,大人。”将士抬头细看,的确是户部侍郎,旋即开了门。
将离满头汗:“你倒会拖人下水。”
“同你学的,把水搅浑不是侍郎你的绝活吗?”
“承让,承让。”
夜马疾驰,繁星如雨落在身后,前路是一片黑暗。
树无影,风无声,二人在马背上沉默着,将离还在思索李承昊要带她去哪里,马蹄就戛然而停,落在了浮云山脚下的空地。
淡云掩着清月,滩流小溪在月下如浮动的白缎潺潺而过,绕着浮云山最后汇聚到未央湖去。
溪旁有颗枯木,枝桠如巨兽张着獠牙。
她尚未站定,凌厉的掌风就毫不客气地袭来,一双冰眸在夜风中如饿狼的眼睛。
她是今夜的猎物,李承昊志在必得:“别挣扎,死了爷爷给你埋。”
将离俯身避开,月色映着她半边脸,眸光璀璨:“谁埋谁还不一定呢。”
“我父子同你父子还真是命里相克,屎盆子一个扣一个,没完没了了。”
北冥在他的心里重如山,容不得他人诋毁;他不是雀都的狗,他是北冥的狼。
宁可站着死,绝不跪着生。
“来吧。”将离知道他憋着气。
这个架必须打,她要收复李承昊。
她素来干脆,先发制人,一脚踹中李承昊的胸口。
力道很大,李承昊后退了两步,夜风带起了他的袍角,藏在夜色中的笑像是冰冷的刀:
“狗东西。有种冲我来,弄我爹算什么本事。北冥儿郎驻守边境吃糠咽菜,雀都的狗还啃着肉骨头呢!”
他挥拳朝向将离面门,将离身子一矮轻松绕过,李承昊抬脚直攻下路,将离半身腾空向后一退,片叶不沾身。
李承昊眸光微亮,脚下画着圈,猛地一跃做了个假动作,朝将离扑来;将离一时不防备,被他扑倒在地,死死压在了身下。
李承昊阴谋得逞,大手攥着衣领,唇角上扬:“说遗言吧。”
“疯狗。”将离挑着眼看他,黑眸丝毫不乱,反而满满都是戏谑。
李承昊又开始恍惚,两双眼睛不停地重叠、吻合,再重叠,他难以掌控,这感觉比将离眼神的挑衅还让他难受。
迷惑化成了愤怒,一拳朝她面上挥去。
将离眼也不眨,拳头偏落在俏脸旁的地上,尘土飞溅,细碎地沙土飞进将离的眼。
她闭上眼时,身侧那堵墙跟着颓然倒下,轻吁怒骂:“臭小子。”
夜鸟高飞,枝桠沙沙。
两人都没有再说话,唯有胸口处起起伏伏,气息逐渐从急促转至和缓。
“怎么不打了?”将离手枕在头下,抬眼望着天。
星辰闪烁,银河如练,山野清风徐来,将往事一帧帧翻过,不过是短短月余,却像是过了半生那么长。
他们都被命运推到刀尖上,由不得他们不走。
“说说吧,背后是谁。”李承昊嗓子发哑,酒意随着血液游走,他比过往更清楚,眼前的人不是敌人。
“叶小东是涌安杀的,北冥剑也是他放的。当夜若不是你缠着我,兴许我能跟上他。现在……”她偏头看了一眼李承昊:“死无对证了。”
李承昊也微微偏头回望,二人目光交织,彼此都能感受到无声地坦诚,“继续。”
“所有的事都从太傅的死开始,你入京为质,再用非法屯田参北冥,激化李将两家的矛盾,破坏太子与北冥的关系。你我都是这局中的棋子。”
“太傅之死,孟贺嶂的口供,钉死了北冥的疏忽之责;屯田案,是工部汤宪亲点的我来办的差事;叶小东的死,你命好,遇到了我。要不然也要跟着二皇子一并搅和在这乱局之中。他有卫家在身后保着,你呢?孤身一人,还不是任人宰割,连带着北冥王也要被抄家灭族了。”
将离半坐起,语重心长地拍了拍他的肩,挑着眉:“是不是得给我磕个头?”
嘁,李承昊轻笑,“脸真大,自己贴上金了?”
他那日不过是一时失神罢了,太子想围他也没那么容易。
将离笑了笑,趁着空隙她抬手收拾好凌乱的头发,雪白的脖颈在月下发着光;
藕臂轻晃,带起一阵风轻轻撩过,李承昊心头的某一处变得柔软。
他的视线落在她手臂长长的红痕,剑眉紧蹙:“谁打你了?”
将离茫然地低头看他,李承昊坐了起来,一把抓住她的手,掀开了袖子:“鞭子抽的?”
啧,他手指粗粝,虽然只是轻触,将离却疼得倒吸了口冷气。
伤痕忘记擦药,好几个时辰过去都红肿了。
“小伤。”她抽回了手,微微红了脸。
李承昊不自在地撇嘴:“可别赖我。”